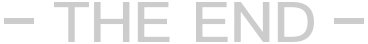童话
童话,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童话具有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特点。童话常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生命,使其拥有人的思想感情。
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作家创作的,著名的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豪夫童话》,英国的《王尔德童话》。另一类是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后经有心人搜索、整理而成的,著名的有《格林童话》,如《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等,都选自于它。
文学概念
简介
“童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童话”一词在《辞海》中的基本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性格的成长”。
综上所述,所谓童话是儿童文学体裁之一,通过丰富的幻想和夸张、象征、拟人的手法塑造形象,以适宜于儿童阅读的作品。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像、幻想和夸张编写的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童话的基本特点有: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编写;有独特的修辞手段,如象征、比喻等。对于处于人生早期的儿童来说,他们富于幻想,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非常好奇,没有明确的主客体概念,认为万物有灵,如认为周围的一切都像自己一样,既会高兴也会哭鼻子,也会肚子饿和口渴。因此,儿童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世界的方式。为了帮助儿童认识周围的环境和事物,就要创造一种既适合他们的心理特点,又利于他们的发展的中介。童话的本质及其对儿童发展的价值正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时,童话也是儿童喜爱的。正如列宁所说:“儿童的本性是爱听美妙的童话的。”

一般童话中有很多超自然人物,如会说话的动物、精灵、仙子、巨人、巫婆等。在现代西方文学的写作方法中,「童话故事的结局」(fairy tale ending)通常指的也是快乐的结局,如很多童话故事中一般有公主和王子。
由于在西方的许多文化中,恶魔与巫婆等童话元素常被认为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这时童话就可能变成传说,接近史诗。在文体上,童话与传说、史诗的主要区别是,童话故事往往会在故事中多加入一些对人、事、物的虚构描述以增强故事性。一个范例是故事开头用「很久很久以前……」来描述,而不是具体的真实时间。
近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童话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文化中广泛被发现。童话故事可以口述或写作的方式存在,但仅有写作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使得童话故事确切出现的年代难以考证。但就可考的文学记录而言,童话故事至少已经存在超过千年。在西方,早期的童话并不被称为「fairy tale」,而是被视为短篇小说的文体。「fairy tale」一词被认为最先是由法国作家d'Aulnoy女士所提出。时至今日,童话故事的流传仍以写作方式为主。
早期「童话」的听众群除了儿童外还包括成人,后来,随着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格林童话》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作品的出现,童话这一文体被正式与儿童相联,并且这之后这种关联性日渐加深。
在童话的分类上,民俗学者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以及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形态分析法。

历史记载
起源
童话故事最初是传统口述民间故事的一部分,通常会被讲述的具戏剧性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相传。因此,童话的历史难以考证。尤其是早期不识字的说书人所说的故事,通常都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可供后世参考。
最早有以文字形式流传的童话故事是在公元前1,300年的古埃及,自此之后童话故事开始在写作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诸如公元100至200年间阿普列乌斯(Apuleius)所著《金驴记》(The Golden Ass)出现的爱神与美女(Cupid and Psyche)或是公元200至300年间印度的《五卷书》,但由故事本身无法得知这些故事是不是反应当时当地社会所流传的民间故事。许多证据显示许多之后童话故事集里的故事都是根据民间故事重新编写而成的。这些故事合集通常根据更古老的民间故事而来,像是《一千零一夜》《吸血鬼的故事》(Vikram and the Vampire)及《彼勒与大龙》(Bel and the Dragon)。除了这些合集之外,中国的道家哲学家,像是列子与庄子,也都将一些童话故事以他们的表现方式出现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而在较广泛的定义中,《伊索寓言》(公元前六世纪)是西方世界第一本著名的童话集。
典故
典故的引用大量出现在杰弗瑞·乔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斯宾塞的《仙后》以及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之中。《李尔王》的故事中被认为引用了大量的童话典故。在十六及十七世纪期间,意大利的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在《愉快的夜晚》(The Facetious Nights of Straparola)一书中重新诠释了西方文学中的故事,书中的故事包含了大量的童话故事,而巴吉雷(Giambattista Basile)的《那不勒斯人故事》(Naples)则全部都是童话。卡洛·戈齐在他的意大利歌剧场景中用了许多童话故事的典故,例如他的歌剧其中有一幕取自于意大利童话的《橘之恋(The Love For Three Oranges)》。与此同时,中国的蒲松龄在1766年他所出版的《聊斋志异》中也收集了许多童话故事。而童话故事本身在十七世纪末叶的法国上等阶层中开始逐渐风行,寓言诗人拉封丹和另一位知名作家查尔斯·佩罗(《睡美人》及《灰姑娘》的作者)两人所编纂的童话故事是其中受欢迎的代表。虽然特拉帕罗拉(著有《穿靴子的猫》)、查尔斯·佩罗和巴吉雷的童话集中包含了许多童话故事最早的形式,但这些编者也重新诠释这些故事以符合文学的效果。
而且首先尝试不仅仅是保存童话故事中的角色个性也同时保留故事风格的,是德国的格林兄弟。但讽刺的是,虽然格林童话第一版(1812年到1815年)是民俗研究学者的宝库,但为了保证销售量及受欢迎的程度,格林兄弟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也开始改写书中的故事。格林童话集的转变不只将内容偏离原有的民间故事,也影响了原有的民间故事的面貌。除此之外,格林兄弟也没有收录一些德国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其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些也曾在查尔斯·佩罗的故事集出现过的故事是法国故事而非德国故事。安徒生的童话最著名。

故事分类
最初故事
最初童话故事的听众除儿童之外也包括成人但19世纪及20世纪之后,童话故事开始渐渐转变成儿童文学的一部份。
包括奥诺伊夫人在内的法国作家群précieuses尝试着将他们为成人所写的作品推广到儿童读者群中。当时的一位女伯爵也宣称她若是仍在孩童时代也会喜欢读童话故事。而后期的précieuses女作家,Jeanne-Marie Le Prince de Beaumont为儿童读者重新编写美女与野兽,她的版本也是今日所流传的版本。而格林兄弟在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出版后,也为因应读者的抱怨而将他们的故事重新改写为较为适合儿童所阅读的版本。
现代故事
在现代,童话故事已转形成为适合对儿童说的版本。为了让童话故事更适合儿童阅读,格林兄弟也致力在减少故事中对性的描述,在第一版格林童话中,长发姑娘在几次王子的深夜造访后开始问巫婆为何衣服越来越紧因此巫婆知道长发姑娘已经怀孕,但在接下来的版本中,则修订为较容易拉上王子而较难拉上巫婆。然而后续的版本在暴力方面(像是对坏人的惩罚)反而是增加了。但托尔金也发现,为更适合儿童阅读,杜松树(The Juniper Tree)故事中的食人者的烤肉串曾在其中一个版本中被剔除。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由于时代背景之故,故事往往会被改写的带有教化意味。例如狄更斯就曾对灰姑娘故事中所出现的禁酒令表示抗议。
为儿童而制作的童话改编在二十世纪之后依旧持续的进行着。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就是以儿童为主要制作对象。而日本动画《魔法小公主》也是改编自童话故事。
人物形象
童话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达出来的。人物形象是整个作品的核心, 没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无法把作品的基本思想生动有力地传达给读者。
童话的人物形象最为自由和广泛,上至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虫鱼、花草木石,不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有形还是无形、具体物质还是抽象概念,都可以通过“人格化”,作为有语言行动、有思想性格的人物出现在童话中;另外,一些产生于人的想像,只存在于魔幻世界的意想同样也能成为童话的人物形象,比如精灵、海妖、神兽等。当然,童话中更多的是人,古人或今人,本国人或外国人,这个阶段或那个阶段的人。而且,在一些童话中,普通的人和超自然人物的形象,拟人化的各种生物、非生物的形象可以同时出现,彼此交往,共同活动在作者设计的童话环境中。但不管选取什么去充当童话的角色,反映的都是人类的现实生活,它们身上具有的也是各种各类人物的社会性格。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叫一些生物和非生物扮演角色。在选择时,一方面要照顾这些东西本来的形态习惯和自然属性,看看是否与所扮演的各种人类角色有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则要考虑表现主题的需要,而且,童话让哪种角色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题。例如《爱唱歌的小鸟》中选择了小鸟作为自由的化身,国王作为专制的化身。如果把小鸟换成关在猪圈里的小猪,就明显地不合适。而如果把国王换成没有权力、无法主宰生杀大权的艺术家,也同样不合适。小鸟的歌声是自由的歌声,所以才引起国王的扼杀。如果换成可以随意操纵的机器鸟,也就难以产生国王杀死小鸟的情节。
此外,在挑选人物角色时,适当地尊重读者的爱好、民族习惯以及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心理和感情,也是必要的。例如,对老鼠这一形象,中国人与美国人就不同,我们多把老鼠作为反面形象,而美国人则比较喜爱老鼠。又如狐狸往往以狡猾的形象出现,狼则以贪婪、凶残的形象出现。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围墙外的小灰狼》中,小灰狼犹如一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童话逻辑
童话的逻辑性是指幻想和现实结合的规律。所有的童话都是虚构的,但有的读起来似乎入情入理,而有的却觉得牵强附会,原因就在于前者符合童话的逻辑,而后者却忽略了这一点,以至破坏了整个故事的合理性。
童话的逻辑性建筑在假定之上,即作者必须为幻想人物的活动、虚构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一个假设的条件,然后从这一假定的前提出发,使事物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使假想的人物在假想的生活环境条件下,合理地自然地发展。在一些超人体的童话中,并不是随意地让一个平常人腾云驾雾,各种魔术仙法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施展,只有童话人物被赋予超人的能力,获得某种“宝物”,或者当这个人物进入一个足以产生魔法的境地以后,才会发生奇境。
童话的逻辑性能使虚构的故事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就是使假戏真做,使作品获得强烈的艺术真实性。但是,运用童话的逻辑并不能改变童话本身纯虚构的性质,让读者真去相信种种假想的故事,相反,它只能突出童话虚构的性质和作用。科学童话尤其要注意童话的逻辑性,更要符合科学逻辑性,不允许违背科学规律和科学实际的情况存在。

美学形态
1. 荒诞感
这里所指的“荒诞”概念是一种美学意义上荒诞感、荒诞性,概念较为宽泛,与现实生活中所指的荒诞一词有所区别。它涵盖幻想、奇异、怪异、稀奇、善变、荒诞可笑、无稽之谈、难以置信等多种含义。正是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荒诞性,才能使童话产生出趣味盎然的美学效果。荒诞是儿童文学作家用以进行童话艺术创造的手段,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童话中常常离不开强烈的夸张、离奇的幻想、扭曲变形和机智的反讽,其中夸张和想象是最重要的。在幻想世界中,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也能当作事实的体验,按照无限的想象和丰富的表现,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奇幻世界。比如《大林和小林》所表现的世界就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贫富悬殊的世界。为了突出这个社会的荒诞性,作者极尽夸张之能,将人物扭曲、变形,将行为丑化,以极其荒缪的故事来揭示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因此,荒诞的本质乃是透过表面的荒诞,体现出本质的合情合理,因为人们在形象的奇异中,看到和感觉到的是新的和谐统一。荒诞以牺牲“自然可能性”为代价,同时在保全“内在的可能性”中得到补偿,从而创造出一个蕴含着现实生活种种意蕴的,别开生面的幻想世界,因此,出色的荒诞创造的应是一种新的美学意义。
出色的荒诞应该是荒诞得离奇、荒诞得新鲜、荒诞得美妙、荒诞得机智幽默。只有新鲜、别致的荒诞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新鲜、独出心裁之不易也正考验着童话家的敏锐性、机智感和创造力。此外,荒诞还可以通过怪诞和滑稽表现出来。事实上怪诞和滑稽常常也是同时出现,表现一种意味隽永的笑趣。比如挪威作家埃格纳的童话《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就是一篇妙趣横生、以滑稽反常出名的作品。
2. 象征
作为一种美学形态,象征通常是指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进而表现或暗示出一种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丰富、深邃的美学意境的表现方法。因此,象征艺术的基本特征应是:首先它具有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而不是只有局部、甚至孤立的细节形象;第二,它应能表现或暗示出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深邃、丰富的美学意境。也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个形象的简单比附、单向譬喻,而要有多义性的哲理内涵,应是具象与抽象的深层融合。
我们知道童话幻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是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透过表象看本质,我们又会发现,在这些奇异的世界中又处处闪耀着现实社会的折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哲理和思想情感。无论是安徒生所创造的海底“人鱼世界”(《海的女儿》);还是张天翼笔下的“唧唧王国”(《大林和小林》);或是郑渊洁所畅想的“魔方城”《魔方大厦》,都具有很深刻的现实象征寓意。
因此,我们说童话应是最具有象征涵义的文体类型,童话的象征隐喻之美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美学特质。这一特质可能与童话和寓言同出一源有关。在中国古代,童话与寓言原本混淆,在最初的古代寓言中包融着很多童话性很强的作品,只是后来才将那些故事单纯,喻意鲜明的作品划归为寓言,而将那些故事性强的作品划归为童话,并开始了分道扬镳的各自发展,但寓言的象征隐喻之美却为童话所保留下来,成为童话的又一突出的美学表现。当然,童话既然脱离了寓言,其象征的美学涵义也必然有所不同。寓言的象征更倾向于运用譬喻,通过喻体和被喻体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来体现其象征性。而童话的象征是整体寓意和抒情经由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体系而获得实现的。幻想和现实融铸成一个象征的实体,含蓄、凝炼、深沉、隽永,象征的结构形态有机地牵织着童话的题旨与美学价值的实现。《海的女儿》中的那个美丽的海底世界不正是表现了人类对于美好爱情和崇高精神品质的渴望与追求吗?《大林和小林》中的那个光怪陆离的“唧唧王国”不正是对资产阶级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丑恶本质的最深刻地揭露吗?就是那个《魔方大厦》中变化多端的“魔方城”也是表现了现实中孩子们对自由快乐的游戏精神的倾心向往和自由追求。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写都极其自然地构成了这些童话的意蕴中心或思想灵魂,使童话中所传达的人情与哲理都更加深化了。
以整体所具有的象征美学意蕴为前提,童话中的象征在不同的作品中常呈两种类型:一种更倾向于具象象征;一种更倾向于总体象征。所谓具象象征,一般是借助于一些特定的具体形象并以之为核心,来组织作品的整体形象体系。总体象征,这一类童话的象征涵义并非来自某一特定具象的提携或渗透,而是来自总体形象体系本身。这总体形象体系同时具备作品的表象演绎与内涵体现两方面品质。
3. 喜剧之美
喜剧的美学涵义在最初是以揭露丑的嘲笑为其特征的,在笑声中烧毁一切无价值的、虚伪的、丑恶的东西。但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喜剧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既有揭露批判嘲讽的笑;也有善意讽刺的笑;还有纯粹是娱乐幽默的笑等等。而童话中的喜剧方式通常更多地表现为童趣与幽默的美学特性。这是由于童话特定的读者群的年龄特征所决定的。
在喜剧中,讽刺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对于喜剧童话来说讽刺同样是把锐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讽刺童话最杰出的代表。它把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者。但我们又不难体会到这出讽刺喜剧所特有的童趣意味。同样,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也是一出充满了童趣色彩的喜剧,通过大林和小林这对双胞胎兄弟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来揭示两个阶级尖锐的矛盾冲突。
从以上两篇童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童话喜剧美的特点是与儿童化和童趣化不可分割的,但童趣化并不意味着童话的主题和内涵就是浅层次的,在表面热热闹闹的童趣中,实则隐涵着非常深厚、丰富的现实寓意,这便是童话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童话喜剧美的独特理解所然。从《皇帝的新装》《大林和小林》中,我们都能看到作家这一深厚的艺术功力。
当然,童话中的喜剧也并非都是讽刺敌对的或坏人的,也有对人民内部或孩子身上的缺点进行善意讽刺的,同样可以表现得童趣盎然。比如米哈尔科夫的《狗熊捡了一个烟斗》,这篇童话讲述了一个狗熊抽烟上瘾,以至最后瘫软,束手受擒的有趣故事。
当然,童话中的喜剧美有时候也并非一定要用闹剧的形式体现出来,它甚至还可以用浪漫的诗情来演绎。比如美国作家里昂尼的童话《菲勒利克》,就是一篇充满了浪漫童趣色彩的童话,写了一只富有诗人气质的小田鼠——菲勒利克用他美妙的想象给家人带来快乐的小故事。
童话喜剧美的色彩还可以通过转换视角的手法来加以体现,比如用儿童的视角或用动物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当作者完全视儿童或动物的视角为正宗时,那么原本正常的世界就会变得充满了喜剧味。童话中的喜剧美也可以用纯粹趣味性的表现手法来体现,不强调作品的主题意义,而只是让孩子们在笑声中得到快乐,注重的是一种愉快的游戏精神。喜剧美在幼儿童话中的表现又通常通过童话人物稚拙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来体现一种大巧若拙、趣味盎然的艺术韵味。喜剧美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童话中也并无定律,但总体来看,其本质多少总是与笑、与趣味、与幽默是分不开的。
4. 悲剧之美
尽管儿童文学的总格调是倾向于欢快明朗的,但也并不排斥反映生活中悲剧的一面,因为生活中总是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方面,悲剧是难免的,即使儿童生活也不例外。关键是如何表现悲剧,和怎样表现悲剧。对儿童文学和童话来说,或许更多的不是采取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主要是通过悲剧来展示一种崇高悲壮之美,体现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它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美的注解。而且对悲剧人物命运的展示,还尽量采取一种弱化或淡化悲剧性的表现手段。不像成人文学那样尽量来强化悲剧的激烈冲突。
比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童话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悲剧童话。但这两部童话都写得极美,“小人鱼”为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王子却混然不觉。最后在为爱而作出的生死抉择中,“小人鱼”又为了成全他人的幸福甘愿使自己化为泡沫。这里“小人鱼”的悲剧命运被尽量弱化了,突出的是她对爱的执着追求,以及为爱而献身的纯洁、高尚的精神品德,表现出美学理想的崇高境界。
童话中的悲剧美的表现也可以用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手法来展示其崇高悲壮之美,突出其理想的精神境界。比如英子的短篇童话《到非洲去看树》就是一篇特别富有浪漫幻想色彩的悲剧作品。
童话有时候也表现一些儿童生活中的悲剧,其表现更是采用弱化悲剧结局、注重情感与精神境界的渲染。这一点在幼儿童话中特别突出。比如谢华的幼儿童话《岩石上的小蝌蚪》就是以其悲剧美的心灵与情感的巨大冲击波征服着小读者,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然,童话的悲剧美还可以用喜剧化的手法来表现。也就是故事本身充满了喜剧味,然而,悲剧性的结局却又十分耐人寻味。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米哈尔科夫的童话《狗熊捡了一个烟斗》,就既是一篇充满了喜剧味的十分幽默谐趣的童话,而同时它的结局又是悲剧性的,以悲剧性的结局来告诫孩子们一定的生活哲理。狗熊抽烟上瘾,恶习难改,以至终于一天天把良好的天赋条件糟蹋怠尽,而最终成为守林人不费吹灰之力俘获的战利品。狗熊的悲剧结局的确让人既好笑,而又品味再三。
注:本名词内容引自百度百科